

开学了。
我们升入了六年级。
新教室真是宽敞亮堂啊!这教室的进深比从前的小土屋教室大了一倍哩,红砖墙玻璃窗子,窗子还是往外开的呢!坐在这样的大教室里,同学们都不由自主地挺直了腰板。
教室里的桌椅也换成了崭新的,宽敞的桌面上刷着一层明亮的清漆,几乎能照出人影儿来了。这下子,我们可舍不得在上面画“三八线”了。
教室外墙壁上有几个大字——“百年大计,教育为本”,那字有笸箩大,个个挺拔漂亮。同学们仰着头,对这些墨汁犹新的大字指指点点。
“那可是我哥写的哟!”我挺挺胸膛,骄傲地站在人群里说。
“你哥又不是你!”有福在我身后嗤了一声,“你不就是个鸭司令嘛!”
身后顿时传来了一阵哄笑。
我咬咬牙,握紧了拳头,正想跟他理论,鲁老师夹着书本走过来了,她身后跟着一个女孩。
“同学们,这个学期啊,咱们班上转来了一个新同学!”她转身把那个女孩儿拉到前面来。
咦,这不是脆脆吗?
这回她穿了件崭新的粉红色“的确良”连衣裙,看上去更像一朵亭亭玉立的莲花了。所有的人都注意到,她脚上穿着的可是一双时兴的白球鞋,帆布鞋面雪白雪白的。我们大部分同学的脚上穿的都是自家妈妈做的松紧口的黑布鞋,这白球鞋可是我们的梦想呢!
见大家都把羡慕的目光投向她的球鞋,脆脆有些羞涩地缩了缩脚,悄声对身旁的我说:“这是我姨父姨妈特地到县城给我买的……”
这时,鲁老师拉了拉脆脆,“快,向大家介绍介绍自己吧!”
脆脆转动着酒窝微笑着,大大方方地说:“我叫柳脆,大家可以叫我脆脆,以后请同学们在学习上多帮助我呀!”说着,她弯下腰,深深地鞠了个躬。
我抢着说:“可不是翠鸟的翠,是嘎嘣脆的‘脆’!”
大家都用异样的眼光朝我看过来。
“咦?宽子,你们以前认识吗?”有福投过来的眼神很是特别。
我的脸上有些热了起来,正不知道该怎么回答,脆脆利索地说:“我和宽子早就是好朋友了!”
“哦——”同学们发出了一声意味深长的怪叫声。
我顿时浑身不自在起来。
开学了,放驴子的任务照样不能懈怠。每天放学后,我都会带烟囱到田野里去吃鲜嫩的野菜。
我爹显然很喜欢烟囱,他总想亲近亲近它,但每次都被我拦住了。我还在生他的气,偏不让他碰我的驴子,那可是我用自行车换来的!我爹只好苦笑着摇摇头,咂着嘴在旁边看着我为烟囱刷背、饮水,跟烟囱玩耍。
这天,我刚牵着烟囱出了村,就遇到了有福他们。有福和板凳、网子正在骑着自行车溜坡。
真是冤家路窄!
果然,有福很快便凑了过来,“哟哟!”他打量着烟囱,“鸭司令变成驴掌柜了?你的自行车呢?”他嘲讽着,专拣我的痛处戳。
“驴掌柜——嘎嘎嘎……”网子笑起来的声音像鸭子的叫声。他在旁边笑得前仰后合,那一双细细的小眼睛眯成了一条缝。
网子是棵墙头草,谁有好玩的就跟谁好。那时候,他还央着我教他打乒乓球呢。
我白了他一眼,懒得理他。
我知道,为了玩自行车,好多男生都围绕在有福身旁,我被他们孤立起来了。
板凳却没有笑。
他走过来,摸了摸烟囱的耳朵,“这驴、驴子可真、真神气哩!”
“它叫烟囱。”我告诉板凳。
“烟!囱!”板凳凑近烟囱的耳朵大叫了一声。
烟囱被他吓了一跳,浑身一激灵。
这下我有点生气了,上前便推了板凳一把,“你那么大声干吗!烟囱又不是聋子!”
板凳有些不知所措,“对、对、对不、不起……”他越发地结巴起来了。
我朝他啐了一口,拉起烟囱便走。
身后又传来了有福和网子的一阵爆笑声。
虽然我被有福带领的那群男生孤立了,但我并不孤单,有脆脆跟我玩呢。
脆脆和春桃总是来看烟囱,她俩可喜欢烟囱呢。春桃是班上的学习委员,她是鲁老师的心腹,平日里挺傲慢的。从前她可不屑于理我们这些男生。
她们总是想方设法地编出各种漂亮的花环,挂在烟囱的脖子上,打扮它,然后咯咯咯地笑个不停。
烟囱对她们两个特别随和,无论她们怎么打扮它,它都不发脾气,还热情地配合着,总是用一双湿漉漉毛茸茸的大眼睛笑眯眯地看着她俩。
但有一次,脆脆她们可见识到了它的倔脾气。
这天,我和脆脆、春桃在湖边的沙地里玩。我们玩起了沙子城堡的游戏,玩得不亦乐乎。我把烟囱拴在一棵老柳树下,几乎把它给忘记了。
天快黑的时候,我们玩够了,才想起烟囱来。
我想起还有很多作业要做,便着急起来。但烟囱却跟我赌气,我越催它,它越磨磨蹭蹭地不肯走。
“它一定是嫌咱们刚才冷落了它。”脆脆说。
春桃点头,“是哩,宽子把它拴在这里,吃不到鲜嫩的草,它一定特别生气!”
我知道自己错了,一个劲地向烟囱道歉。
烟囱先是慢腾腾地走了几步,一会儿嗅嗅路边的野草,一会儿追着蚂蚱跑,一会儿又胡乱地去踏进人家的庄稼地里,还在田垄上慢条斯理地留下几个热烘烘的驴粪蛋,气得我用一根秫秸用力抽了它一下。这下子,它更不干了,索性“咕咚”一声躺了下来。
看着它耍赖的样子,脆脆和春桃笑得不行。
但很快她们便不笑了。
无论我们怎么哄它骂它,它就是不肯起来。天已经渐渐地黑了,村子里婶婶大娘们呼唤自家孩子吃饭的声音此起伏彼,脆脆和春桃也有些焦急了。
我眼睛转悠几圈,想出个对策来。我对她俩耳语了一番,我们三个交换了一下眼神就丢下烟囱,往村子里走去。
我想等我们走远了,烟囱一定会沉不住气,悄悄跟上来的。
我一边走一边侧耳听着身后的动静。
你们猜怎么着?这头驴子简直倔上天了!
我们走了好远一段路,它依然悠闲自得地躺在那里。脆脆焦急起来,“这可怎么办啊?咱们也不能真的扔下它呀!”
“这么晚了,回去我妈会骂死我的!”春桃抹起眼泪来。
那天晚上,我爹来牵它,它不走。锅炉叔来牵它,它还是眯着眼睛不动弹。这个家伙软硬不吃,用棍子抽它,它夸张地“啊儿——喂”“啊儿——喂”地大叫着,就是不肯爬起来。用它最爱吃的东西引诱它,它咕咚咕咚地咽着口水,伸长脖子抢着大家手里的甜菜,但还是不起来。
所有人都急得团团转,它就在那里气定神闲地躺着。
“你究竟怎么得罪它了?”我爹和锅炉叔折腾累了,都来责备我。
我委屈地大哭起来。
后来,这头驴子是被抬上小推车,推回家的!
不过,烟囱虽然犯起倔来让人抓狂,但它平日里还是挺可爱的。有一回,它甚至认起亲戚来了。
那天,我带它在堤坡下面吃草,堤坡的拐弯处走来了一头驴。
这头驴被牵在一个头上包着白头巾的老伯手里。我看了一会儿,有点想笑。那头驴和那个老伯长得可真像哩!老伯头发乱蓬蓬的,穿了一件带纽襻的灰布长褂,背有点驼。他手里牵着的驴子看上去显然年纪也不小了,一身干蓬蓬的赭灰色短毛,像深秋被风吹乱的干枯的野草一般。那驴子背上驮着一个鼓囊囊的麻袋和一条白布褡裢,它的背也是那样疲沓地拱着。
一人一驴都迈着慢腾腾颤悠悠的步子,一点儿也不着急。
烟囱站在我身边,支棱起耳朵,背挺得直直的,眼睛紧紧地盯住渐渐靠近的这主仆俩。等他们走得近了,烟囱突然兴奋地跺起蹄子来,还不时拱拱我,一副无比激动的模样。
灰驴和他的主人朝我们这边看了看。
呀,这主仆俩的眼神竟然也是那么相像!那是一种什么样的眼神呢,我也形容不出来,我就觉得像秋天,对,像秋天的天空!有些深远,有些辽阔,又有些让人捉摸不透的平静和从容,还有一些疲惫,但那疲惫却又是那么无所谓的疲惫,可以休息也可以不休息的疲惫……
嗐,我竟然在他们的眼睛里走起神来了!
但是,谁说人家是主仆俩呢?为啥不是老哥俩呢?
这时候,烟囱显然按捺不住了,它撒开蹄子,欢快地跑了起来,迎上了对面的老哥俩。那架式,就像热情地迎接来自家串门的亲戚一般。
但这亲戚却并没有热情地回应。
当烟囱跑到那灰驴身边,兴奋地甩着尾巴,笑眯眯地凑近时,那灰驴却冷淡地闻了闻烟囱,喷了个鼻子,把脸转了过去。烟囱围着那灰驴转了好几圈,灰驴慢腾腾的步子并没有停下来,它并不搭理烟囱,目不斜视地往前走。
那个老伯朝我这边问:“小娃子,这黑驴儿是你家的吗?”
我点点头。
“看这骨架子,以后可是个中用的好牲口呢!”他自顾自地点着头,不再看我,倒背起一只手,兀自往前走。
他俩的背影也那么像呢!无缘无故地,我觉得他们俩都像老道士,其实我并没有见过老道士,但就是有这种感觉。
烟囱跟在人家老哥俩身后,走了很久。
我并没有喝住它。
它是不是想念它的家人了?
我的心里忽然轻轻地一酸,就像咬破一只野葡萄时,舌尖上泛起的酸涩一样。
好一会儿,烟囱才蔫头蔫脑地折回来。它看起来十分失落。后来的整个下午,它都有些不开心,不低着头啃嫩草了,也不快活地跳沟了,只是呆呆地望着一个地方,眼神很是空洞。
我能理解烟囱的心情!
那时候我被爹妈从燕西塘接回羊角洼的时候,特别想念我姥姥和我姥爷,特别不开心,天天爬上房顶去,朝燕西塘的方向望。
何况,烟囱是背井离乡,离开了所有的驴子亲人来到我家的。
我默默地陪在烟囱身旁,在堤坡下的草丛里坐了整整一个下午。我暗暗地想,我一定要把烟囱当家人一样对待。
驴子毕竟是驴子,过了一晚上,它就忘记了前一天的忧伤情绪,又快活地打起滚来。
几天后,我又想起那对长相和神态都特别相像的老哥俩来,我扳过烟囱的头来仔细地看,我会不会也跟它越长越像呢?
说实在的,烟囱这双毛茸茸的大眼睛真的跟我的眼睛很像呢!我长了一对亮亮的大眼睛,还有让女生都羡慕的长睫毛。我的一对大门牙,也跟烟囱的大板牙很是相似!连肤色也像!整个夏天,我的皮肤也晒得黝黑黝黑的,黑得发亮。
但是——我的脸盘是圆圆的虎墩墩的,我以后可不想长成烟囱那样的大长脸。
这些日子,我发现脆脆挺奇怪的。我常常发现她独自站在湖边的高岸上,踮着脚往远处望。每当我上前跟她打招呼的时候,她总是不吭声,转过头去,悄悄地抹两把眼泪。
这让我想起了夏天在荷塘里的那次。不知道她究竟有什么沉重的心事,我不敢再追问她。她抹过眼泪,再转过头的时候,脸上便又挂上了往常的微笑,两个酒窝又滴溜溜地转起来了。
我心里一直留着一个好大的疑团——她可真是个怪人哩!
即使没有脆脆和春桃跟我玩,我一个人跟烟囱玩,也不孤单。我从来不骑它,总是与它并肩走在一块儿——谁会骑在自己好朋友的背上呢!
这天傍晚放学,我带烟囱到了湖边。烟囱喜欢吃水葫芦,我常到湖边用竹钩钩上些水葫芦来给它吃。
这天,烟囱埋头吃起水葫芦时,我便独自玩起了竹蜻蜓。
这竹蜻蜓是用木片削成的,一根细长的木杆子撑起了一对硕大而扁平的翅膀,在阳光的照耀下,一副振翅欲飞的样子。
起初,无论我怎么用手掌搓,它都会一头扎进草丛里。试了好半天,那竹蜻蜓终于旋转着腾空而起,在风中,像一架小飞机在飞翔!
我开心极了,“噢——噢——”地叫着,追着竹蜻蜓跑。烟囱也快乐地踢着脚,跟在我的身旁。
突然刮来了一阵小旋风,哎呀,不好!我心里暗叫一声。果然,我的竹蜻蜓忽悠悠地朝湖里飞去,掉进了湖水里。糟糕,我的竹蜻蜓泡了水,可就飞不起来了!
我心里一急,想也没想便“扑通”跳进了湖水里,这声音很大,哗啦一声溅起一大片水花。
作为一个平原上的孩子,我虽然不是旱鸭子,但也只会狗刨。据我哥说,我的狗刨姿势极为难看,头像鹅一样抻着,扑腾起的水花能有几米高,而且游得非常吃力。别看我在岸上跑得贼快,又灵活敏捷,玩啥游戏都得心应手,但一到了水里,便觉得那清凌凌的水简直像一盆糨糊,我的手脚都被粘住了,扑腾好半天才能游上一两米。我哥说这湖水是静止的,要是到了河里,逆流的话,我不但不会前进,估计还会一直往后退。
况且,自从禁止游泳后,我已经有一年多的时间没下过水了。
这个时候,我可顾不上我的游泳技术的问题,我扑腾着水花,慢慢地朝我的竹蜻蜓靠近。我心里越急,那水便越纠缠我。我手脚并用,使劲地划着水。但我却眼看着我的竹蜻蜓在风的吹动下,越漂越远了。
我急得哇啦哇啦地大叫,烟囱也在岸上“ 儿啊——
儿啊—— 儿啊——”地叫了两声。
儿啊——”地叫了两声。
这时,我觉得身边的水面一阵晃动荡漾,我转头一看,竟然是烟囱!
它静静地浮在我身旁的水面上,它什么时候下来的?它下水的声音竟然悄无声息,我惊讶极了,我第一次见到驴子会游泳,而且像个娴熟的游泳高手!
我目瞪口呆地看着烟囱,它似乎有些得意,朝我眨了眨眼睛。我一时间惊呆了,只顾着看驴子游泳,竟然忘记了自己也在水里,我的身体猛地往下沉了沉,被水呛了两口,我连忙手脚并用,扑腾起来。我溅起的水花洒了烟囱一脸,它不满地使劲抖着耳朵。
“烟囱!”我喘着气招呼它,“游过来!”
烟囱很听话,悄无声息地靠近我。
“烟囱,你游泳这么好,能搭我一程不?”说着,我把胳膊搭在了它的脖子上。
我的身体在水里陡然轻盈起来。
哎!这种感觉可真好哩!
“走,烟囱!”我快活地朝那远处水面上打转的竹蜻蜓指了指,“把咱的飞机捉回来!”
就这样,我搭着烟囱,很快便捞回了我的竹蜻蜓。
我一点也不着急上岸,又搭着烟囱在湖里转悠了一圈,心里美滋滋的,这真是一只活泳圈哩!我开心地唱起了歌来。
烟囱真是一只身怀绝技的驴子呢!
这时,岸上传来一阵惊讶的叫声,原来是老多。他肩膀上背着柳条筐,看来是来打猪草的。
“宽子!”他兴奋地朝我挥着手,“呀,你的驴子可真棒呀!它竟然会游泳,还会带着你游嘞,呀呀呀……”
老多之所以叫“老多”,是因为他话多,向来爱多嘴多舌。他成功地继承了他妈巧改嫂子的“优良传统”。巧改嫂子是村里有名的“大喇叭”,只要她知道的事情,很快全村就都知道了。
果然,第二天,班上便传遍了。
很多男生都簇拥住我来打听,“宽子,你的驴子真能当游泳圈?”
“下回能让我们试试不?”
“那可就棒极了!”
这个时候,我得意极了。
有福站得远远的,撇着嘴黑着脸看着好奇地围住我的同学们。
可是后来,我再想让烟囱下湖游泳时,它犯了倔脾气,再也不肯下水,任我怎么哄它骂它诱惑它威胁它,它要不就直直地站在岸边,用轻蔑的眼神看着我,要不就是抵着脚,委屈地“儿啊儿啊”大叫……我试了好几次,都不能成功。
唉,好吧!
我想,那天烟囱一定是怕我溺水,才下水去救我的。
我这么想着,就不再为难烟囱了。
虽然烟囱没有载其他同学下水玩过,但他们却也喜欢起我的驴子来了。我再去放驴子的时候,树林、老多他们总是会跑过来,跟烟囱一块儿打滚、跳沟、赛跑……
我还拿出我的新弹弓来,跟他们一起玩。
姥爷做的那把弹弓可真精致呢,弹包结实,牛皮筋弹力十足,木头把手打磨得光滑细致,还上了一层红油漆呢!
这把弹弓就像当年我那把木头手枪一样,很快便吸引了伙伴们的心,抢手得很。我们用这把弹弓射麻雀,射水鸟,射树尖上最高的那片叶子……
有时候,我也瞄准远处的有福。他推着自行车,背影有些落寞。我眯起眼睛,瞄准他的屁股,“啪!”我嘴里喊一声,却并不把弹子射出去,惹得大家一阵哄笑。
但很快,这把带劲的弹弓惹了祸。
那是个星期天,午后,我牵了烟囱准备出村去,在街上走着走着,我突然发现前面的墙头上蹲着一只麻雀,它蹲在那里似乎在想心事,一动不动地发着呆。
我一时手痒,也忘了这么做不对,迅速掏出我的弹弓,在皮弹包里放了一颗空心小珠子,手一用力,子弹嗖地射了出去。我看到那块小石子擦着那只麻雀的翅膀尖滑过,麻雀惊慌地扑棱一下飞走了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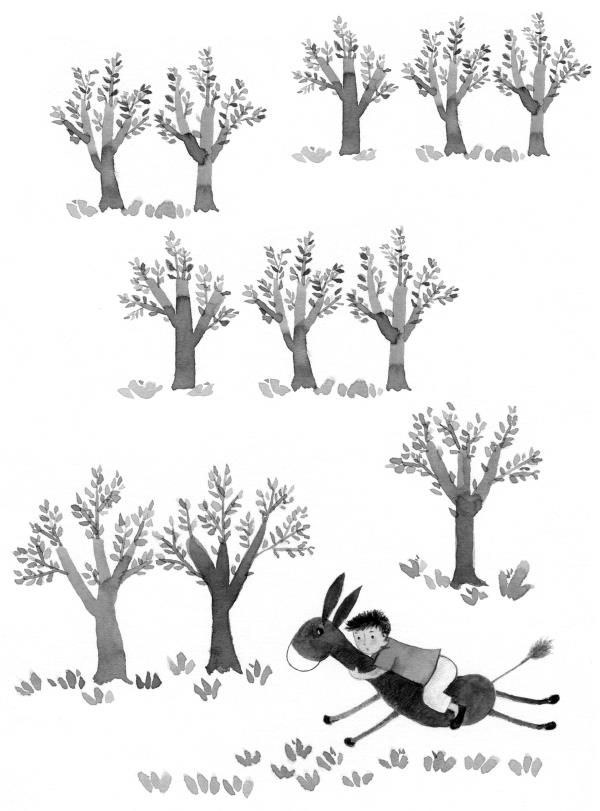
“走!烟囱!”我叫道,“去追那只麻雀,我打着它的翅膀尖了,它跑不了!”
那只麻雀负伤,歪歪斜斜地飞得很不自如。我一路仰着头,追着它。它终于在一个枝头落了下来。我把浑身的力气都用在了手臂上,又一次射出了我的子弹。
“看你往哪儿逃!”我心里暗叫了一声。
“扑!”
耳边传来了一声闷声闷气的怪响,我定睛一看,哎哟喂!我的心顿时凉了!
我这回射出的子弹也太偏了吧,射中的竟然是一只胖大的葫芦。那葫芦下半截已经完全被我打烂了,白嫩的瓤连同籽粒一块儿掉到了地上,一塌糊涂。
我惊呆了。
要是别的葫芦也就算了,那个葫芦,可是这家的主人蔡爷爷的宝贝啊!他一直小心地莳弄着那条葫芦藤,把其他的小葫芦全都剪掉了,唯独留下这一个大的,他说,要让这个大的吸瓜藤里的全部养分,这样可以长得更好一点!
那个葫芦也真漂亮,形状完美,个头儿巨大,一看便不同凡响。蔡爷爷每天都要笑眯眯地看上他的葫芦一会儿,十分骄傲的样子。他对全村人都说过,等它成熟了,他要拿去让人家在上面作画,画一个八仙过海,放在厅堂里,一定神气得很!
蔡爷爷的神气,就这么被我给毁了!
想起蔡爷爷暴跳如雷的模样,我心里乱成了一团麻。我回头看看烟囱,它似乎察觉到了我的不安,紧张地来回踢踏着蹄子。
果然,傍晚的时候,蔡爷爷捧着那些被打烂的瓜瓤子气急败坏地闯进我家来。他翘着下巴上的白胡子,两只手哆嗦着,把瓜瓤子给我爹看,“你瞧瞧你儿子干的好事!”他带着哭腔叫着,“你看怎么办吧!”
我爹愣了一下,皱起眉头,回头瞪我,“这是怎么回事,宽子?”他的语气里已经明显带了火药味。
我爹一向很严厉又很要面子,没有人比我更清楚了!我知道,接下来,他马上就会抄起灶台上那根粗粗的擀面杖了。我低着头,心里斗争得厉害。“那个……那个……”我搓着衣角,小声说,“那是烟囱咬的,它想吃掉那颗大葫芦……”我的心剧烈地跳动着,声音很不自然,“我发现它偷吃的时候,已经晚了……”
我爹还没等我说完,便大步冲到烟囱身旁,扯过绳子,一把套住了烟囱的脖子,使劲把它拴到院中那棵老榆树上。烟囱看着恼怒的爹,有些惊慌,扭着脖子挣扎着。我爹抄起墙角的一把铁锹柄,朝着烟囱的屁股便拍了下去。
烟囱疼得大叫起来,大嗓门都变了调。
我吓得闭上了眼睛,想象那铁锹柄落在我屁股上的感觉。
我爹又打了几下,烟囱大叫着,蹄子胡乱踢腾着,绕着树转着圈又躲又跑。一会儿,那绳子便紧紧地勒住了它的脖子,它咧着大嘴巴,喘着粗气,“啊儿啊儿”地呻吟着。
它大叫着,一双毛茸茸的眼睛乞求地望向我。它是在向我求救……我的心像被马蜂蜇了,很疼。但我却假装没有看到,扭过头去。
“算了,算了!”蔡爷爷叹着气拉住我爹,“我们不要再跟牲畜计较了!”
我爹回头骂我:“宽子,这次先饶了你,以后再不看好驴子,挨打的就是你!”
我战战兢兢地点了点头。
烟囱替我挨了顿打,我心里很愧疚。晚上,我躺在床上翻来覆去,我反复地想,要是烟囱会说话,它会不会大声地向我爹辩解,揭发我的谎言呢?
它会?它不会?
我心里不停地拉扯着,不知不觉就睡着了。
烟囱挨了打,有几天情绪很低落。但它对我还是那么信任和友爱,它还是用它那滑溜溜的脖子蹭我的头,用软乎乎湿答答的舌头舔我的手。
我觉得对不起烟囱,就故意躲着它,于是,我不再出去疯玩了。一个人闷在屋子里,时间突然多起来,我便从容地研究起作业来。那些数学题目中的人物们可真奇怪,干吗非要把鸡和兔子放在一个笼子里,让我们数脚又数头,借此来为难我们。还有,有些人总是把游泳池里的水,一边放一边抽,简直是一群疯子嘛!
但认真研究起来,倒也挺好玩的。我请教脆脆和春桃,做了一道题目又一道题目,越来越有瘾,不知不觉把所有的作业都完成了。
谁知道,我这一认真学习,反倒出了事端。
这天晚上,我家来了个客人,是一脸严肃的鲁老师。
我爹和我妈热情地招待她入座,鲁老师意味深长地瞥了旁边的我一眼,然后从背包里拿出了两张数学试卷。
一张是学习委员春桃的,一张是我的,全都是一百分。
“呀!”我妈惊喜地叫了起来,“我儿子长出息了!居然能考一百分!真是让人难以想象呢!”
说着,她便要来抱住我。
“我怀疑宽子考试的时候作弊,抄了张春桃的试卷!”鲁老师突然抛出了一句话。
“啊?”
我爹、我妈和我全都愣住了。
我的脸登时便涨红起来,梗着脖子叫道:“我没有!”
“考试的时候我就看到你总是摇头晃脑的,想不到你竟然真的在偷看旁边春桃的试卷!”鲁老师生气地说。
“我没有摇头晃脑,我那是……那是……解出了题目开心起来了!”我又愤怒又着急,说话都结巴起来了。
“啪!”我爹猛地拍了一下桌子,站了起来,他的脸也涨红了,显然十分生气,“你做了这样的事情,还在这里狡辩,真是太丢人了!快承认了吧!”
“我没有!没有!”我哭了起来,哑着嗓子大叫。
我爹举起胳膊,冲过来就要扇我,被鲁老师一把扯住,“有话慢慢说,别动手!”
“是我没教育好他!”我爹怒吼着,“考低分是能力问题,作弊又撒谎可是人品问题!今天我非揍他不可!”
我大颗大颗地掉着眼泪,心里委屈极了,哽咽着喊道:“你们太冤枉人了!”
我一跺脚,转身呜呜哭着跑出了家门。
夜很黑,是没有月亮的夜晚。我的心被一只怪兽拼命地撕扯着,一股热血涌上脑门。我不辨方向发疯似的朝前跑,胸膛里呼哧呼哧地拉着一只大风箱。我跑出了村子,跑到田野里,我横冲直撞地跑了很远,踩过刚出苗的小白菜,穿过棉花田,穿过玉米地……腿被草叶绊住了,使劲地甩掉接着跑,脸和胳膊被玉米叶刺伤了,一点也没感到疼。仿佛只有奔跑,才能将那只卡在心里的怪兽吐出来。
远远地,我听到村子那边传来焦急呼唤我的声音,我的泪水又一次掉了下来,我甩甩头,继续跑。
黑暗里,我也不知道自己跑了多远,直到我筋疲力尽,脚下一软,扑倒在一个土坡上。初秋的夜风已经很凉了,吹着我满头满身的汗水,让我不禁打了个寒战。
这时候,我的脑袋才清醒了一点。
这是哪儿?我望望四周,周围都是密密麻麻的庄稼,高高矮矮的黑影子一层又一层。我爬上土坡望了望,夜空中繁茂的星星向头顶压下来,远处根本望不到村子里的灯光。铺天盖地的虫子叫声像唐僧念的紧箍咒一般,不时,还传来一声声瘆人的大鸟“咕嘎咕嘎”的叫声,恐惧渐渐袭上我的心头。
糟糕,我迷路了!
突然,一个黑影忽地从我身边掠了过去,“妈呀!”我吓得一声尖叫,我的毛孔一下子全炸了起来,起了一身鸡皮疙瘩。那影子扑啦啦地落在了我身后的一丛灌木里,我浑身颤抖着,拔腿就跑。
但是,要往哪里跑呢?我觉得自己掉进了一个可怕的黑窟窿里,四面八方都是路,但又全不是回家的路。
我蹲下来,把头伏在膝盖上,无助地哭了起来。
“爹……妈……你们快来救我啊!”我大哭起来,但又立刻噤了声,我觉得哭声一定会把黑暗里的敌人吸引过来。在这广褒的平原上无尽的黑夜里,一个十岁的孤零零的男孩,一个从小便怕黑的男孩,与一只小蚂蚁有什么区别呢?
我抱着头,想着今天晚上发生的事情,突然一个想法深深地攫住了我的心,它比恐惧更让我心慌。我想起了烟囱,想起那次我逃避惩罚,嫁祸于它,让它挨打的事。我终于体味到了那种被冤枉的滋味,我还能为自己分辩几句,赌气跑走,而烟囱却什么也不会说……
对不起,烟囱,对不起……
就在这时,我的耳边传来了几声远远的“啊儿喂——啊儿喂——”的叫声,是烟囱,它来寻找我了!
“烟囱——烟囱——我在这儿!”
我大叫着朝那个声音的方向跑了过去,烟囱大嗓门的叫声渐渐地靠近了我。
我终于看到了一闪一闪的手电筒的光亮,听到爹妈还有鲁老师焦急呼唤我的声音。
我一下子扑上去抱住了烟囱的脖子。
“幸亏烟囱嗓门大,才找到了你!”我妈一把把我搂在怀里,几乎要哭出来了。
烟囱用它毛茸茸的脸紧贴着我的脸,我惊魂未定的心才渐渐踏实起来。
“烟囱这个家伙,不知道什么时候悄悄追上了我们,它好像知道我们要去找你,也很着急!”我妈拍着烟囱的背说,“好了,找到你就好了,你这个孩子,脾气比驴子还倔啊!一口气跑了这么远!”
鲁老师在旁边有些不好意思地说:“宽子,对不起,那会儿你走了以后,我们又仔细查看了一下两张试卷,发现最后那个难解的应用题,你和春桃的解法是不一样的,你的解法更好!我误会你了,你没有抄别人的试卷,对不起!”
“我们可得好好奖励你呢!”我妈搂住我说。
我爹站在旁边,欲言又止。
这个时候,我早就忘了跟我爹怄气。
我抬起头,咬了咬嘴唇,对我爹说:“爹,有件事我得向你坦白,蔡爷爷的大葫芦是我用弹弓打烂的,不是烟囱,上次你冤枉它了!你罚我吧!”
黑暗里,我爹压着声音说:“也是怪我,不分青红皂白就……”
“这样,我们更该奖励你了!你能勇敢地承认错误,比考十个一百分更重要!”鲁老师说。
“啊儿嗯——啊儿嗯——”
烟囱蓦地抬起头,大叫了两声。冷不丁地,我们都被吓了一大跳,然后,又全都笑了起来。
那欢快的大嗓门,震落了几颗夜空中的星星,它们倏地划过天幕,落进了我的眼睛里。